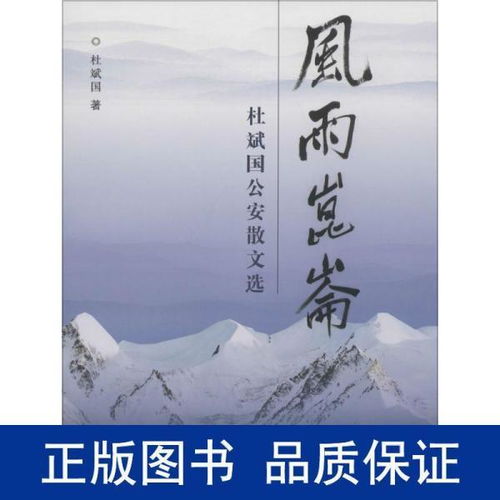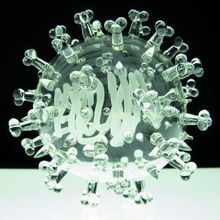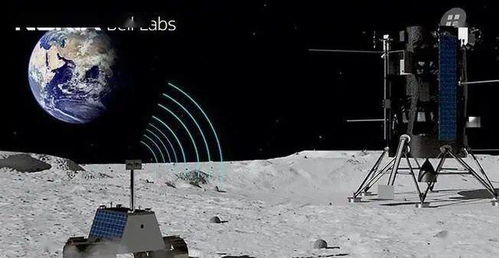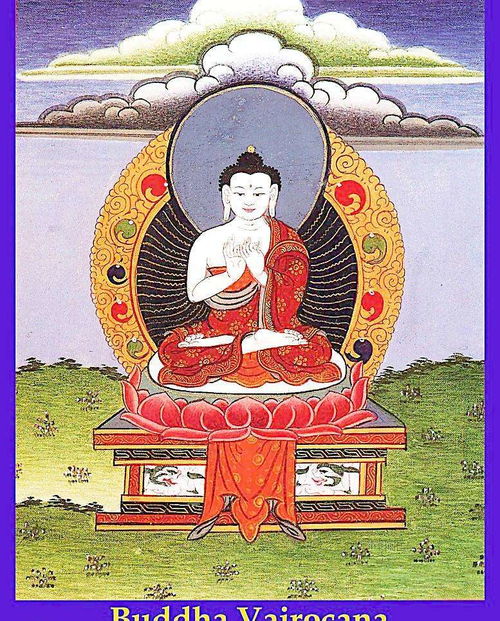(散文荟) 永 近 的 风 景

(散文荟) 永 远 的 风 景
原创: 汴梁客子逸 子逸物语

我一向盼望着本身成熟,不再沉迷被人视去世老或陈腐的风物和头脑。然而,那些大家可以鄙视的工具彷佛早已沉淀铭记在心上,于嘈喧华杂的滔滔尘世中穿透牢牢禁闭着呼吸与魂魄的四面墙壁在梦里重现:缈缈星空里,一双不眠的眼睛;斑澜的月华里,一个又一个品味不尽的故事。隐约延伸,成一条渐明渐暗的乡路。有一个少年,赤足走在上面,湿润的夜露打湿他的裤脚也缓缓润泽着他莫名的骚动与不安。
这些梦乡,总是在寂静地把那些不愿消逝的影象叫醒,成为生命的潮,打击你疲乏的大脑,叫醒你心田深处那陶醉未醒的万千柔情。,这方未被光阴腐蚀的一方净土,永久是春天的景象,迢遥而邻近……
(一)
小小的乡村,被一条弯弯流淌的小河围绕着。有些衡宇就枕着河岸而筑,陈腐的青砖上生满绿苔,瓦棱间长着些叫不着名的荒草棵子,映在水里。有鱼儿上卑鄙戏,竟好像在穿越河底的浅草。河滨,有女人在洗涮,通红的手指,洁白的布衫,另有几棵青菜。屋檐上站满了灰色和褐色的麻雀,在那边展着翅晒太阳,一壁欢乐地唱歌。河里偶然也停一只木排,上面是挽着裤脚的渔人,提着网,有水桶和水漉漉发着青色的撑竿。
当太阳被乌鸦叫着驮进那株高峻的古槐间的窝巢时,街道上开始有孩子飞奔着追逐在薄暮里上下翻飞的蝙蝠。间或,也有一两个穿着破衣游街穿巷的小贩来往追求落脚处:“补盆补碗换桶底,补缀钢精锅哦……大娘,行行好,让俺在恁门过道里住一夜吧。”正低头昏昏欲睡的老妪,干瘦了没牙的嘴角翘一翘,侧耳听见门外的喊叫,便放下拴在树上的摇篮,扭过头。“别吵,别吵,小宝儿还没睡熟——你等他爹返来和他一路睡俺东屋吧,门过道里凉爽得很呢。”千恩万谢的小贩转身去拎本身褴褛的洋车家什,妻子婆便又低下头哼起那发黄眠歌,“咿咿呀呀,唧唧哝哝。”一首无字的歌单调悠久,却又低徊婉转流淌不尽。缠缱绻绵让人痴迷着,不知不觉那明晃晃亮得刺眼的月儿何时就爬上了树梢。
哦,一个幼小的生命栖息在梦幻的温馨里,那悠悠的亲情何等像温和舒缓醇厚平静的港湾。
(二)
暮春季节,人们已没了先前的很多闲散,男人和女人都下地去或种瓜或点豆,或种植棉花。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真象一片海。不消说,风是柔和的,氛围也清新。升沉不定的海浪里的星星点点可不是流落的篷帆,那是穿着五顔六色的人在浮现浮下。鹧鸪鸟和斑鸠在人头上方贴着头皮掠过,啼着冲上天去。一声声啁啾,真如扯破一匹新织的绫绸,碰碎一盏轻松的茶盅,显得那么悦耳动听。
某一块未耕的秋茬地,这时便有一头老牛拉了一张木犁吭唷吭唷地在犁。片刻,长长的一声吆喝,在旷野里悠悠地回荡。而远方地平线的际极,始有黑蚁般的一团在移动。缓缓地,近了。先是如屎壳郎,尔后便更大,像一只狗,像一头驴。再近了,本来是一辆小汽车呜呜嗡嗡,沿着田头那不宽的土路开过来。停也未停,屁股后冒一股烟又溜走了。地里的人都驻足了看,希奇得不可,谈论半天。着末,便纷纷太息,又弯下腰去。旷野里又陷入平静,还是暖和的天空,漂浮着野草的涩涩苦味和野花的淡淡芳香。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是乡间人难过的对大天然的感悟啊。
(三)
这是一个笼着薄雾的初夏的清晨,太阳尚未跃出地面。河面上吹来的微风,带着湿润的凉意,河滩上遮没腿肚的芦草和蒲荻,葳葳蕤蕤。河堤下四五棵不高的柳树,垂下的枝条交错在一路。红、黄、蓝、白、紫,各色的野花开得喧闹,花瓣上的露水闪闪发光,晶莹欲滴。摘一朵放在鼻子下去嗅,那种淡淡的花香有一种无法说出的满意。
向阳从河堤的另一壁浮现来,射穿密匝匝的槐丛。绚烂的云霞溶化了半天,湿润的树色梦般柔软而娇羞。光的乳汁正把浓绿溶解为翠色的雨,一滴,一滴,滴在并肩依偎着的一对牧鹅的男女身上。他们双双走进了岸边的洼地,坐在深深的茅草丛中。飘曳的柳丝抚爱着他们的肩,吹动着他们的头巾和黑发,也拂动了他们平静的心湖。低低的呓语使年轻的血液变得痛快酣畅变得沸腾,涓涓的流水使他们储藏的爱的盼望受到勾引得以萌发。天上是飞舞的云彩,面前是生命的无穷绿茵,也是纯朴的爱的乐园。
啊,这浓厚的富有豪情的发达葱郁天下,是一个诱人而奇妙的童话,让人忘却阴霉的世俗和蒙着尘滓的成规。
(四)
阴悒污浊的穹宇在人们的渴望中缓缓裂开了缝,惨白的天空开始部署下一条条蓝色的“云”。旷野上雾状的气味撩围着,低垂的浓厚的树色则变得疏黄而高瘦。棉桃又开始裂开吐出洁白的棉絮,高粱早已被倦倦的牛车吱吱呀呀地驮去,玉米也被人从腰间夺去果实,站在冷风里呜呜作响。枯干的衰长的秋草粘在地上,任风吹得慄慄发颤。乡人们戏谑着,怅叹着把割下的豆棵胡乱地捆起,背负了从搭起的浮桥上斜斜乜乜地跨过河沟。
连接着菜田的一端便是田舍。无墙无院,几株毛白杨两棵红皮柳,围围着青砖红瓦的屋舍。院火线亩大的坑塘,荷叶已枯,只留下几枝折断的藕茎挺立着。蛤蟆已隐入油亮的坑沿下很少噤泣。瓦屋的侧处,用树枝麦秸加泥巴斜搭的矮棚即是厨房。胸脯饱满的女人用围裙擦着眼角的灰渍,给暮归的男子盛上一碗饭,然后关怀地问一句:“收完了?”男子按例从塞满了的喉咙里“唔”一声,低下头闷声闷气地扒那碗里的饭粒。尔后,抹一下嘴对正凝视着瞧他的女人一呶嘴,“把孩子抱进屋里,别着了凉。”弯下腰搂了一抱柴禾,向着女人喊:“来日诰日朝晨到南地把花摘摘,我计划赶集去。他姥爷生日哩,咱不克不及空动手去。”
昏暗的天缓缓冷静下去,西边天涯横布了一带烧霞,不整洁突突兀兀的,像着了火。深沉博大的暝色在面前正兀自睁开,而那新月儿像刚磨的镰刀一晃一闪也从东边的云层钻出来。草垛边卧着的狗汪汪两声,统统都归于平静。只有未点灯的屋里时常传来几声女人的唏嘘和孩子被奶头塞进嘴里后含糊的呜咽声。
小小的家,是一艘熟睡的船,在秋意微茫的寥寂里轻轻地荡漾。负重的人们在生存的艰苦里极重繁重的喘气着,卑卑怯怯的繁衍着,并在此中岑寂地坚固地追求着生命的实着实在。
(五)
一轮冷月悄然默默地挂在高高的天上,闪闪熠熠。纯静无尘的清辉铺满大地,使乡场上那些方的或圆的麦秸垛变得透彻,变得神奇。青烛似的白杨,枝叶间千光万点迷离扑朔,倏然地狼籍了,斑驳的月华随风舞成一片奇幻的梦乡。地上,未曾融尽的雪已被推到街心,经心地堆砌成悦目的景状,在清澈漫流的月光下,那些耽于理想的淘气孩子用灵活的双手制造着本身的雕塑。
透过紧闭的柴扉的隙缝,隐隐可见屋内火光盈盈,噼噼剥剥。一盆小小的碳火,就营制了一个暖煦煦的氛围,燃映出老的少的朱红面庞。一嗒一嘟的稷茭草和高粱穗刮净后穿成的炊帚把子与长串长串的红紫的秦椒,吊挂在檐下,模糊中泻着一团一团的墨影。而暗中里,却有两只鸽子在孤寂中咕咕地不停相互召唤着本身的爱人,很柔怨,很平静。
哦,墟落的隆冬的夜色,真像一片平静迢遥的海,亘古普通地缈茫幽深。但又有谁能说天籁无声,只有去世寂呢?这种澹泊清幽,让你脱却尘缘,筛失了人间的晃盈与哗闹、喧华与荣辱,突然静化,物我两忘了。
大天然奇诡的灵魂和家乡故乡难以割舍的庞大情愫,使人日思夜想,心旌漂浮。它让你偶然惋惜,偶然激越。在它上面,有灵活的笑,虚幻的梦,芳华的爱的希冀,也有无尽的乡愁。在从古到今的光阴里,闪闪耀烁地牵引着你的心灵,让你淡泊清净,无须费尽心血。在它的度量里,你梦的精灵自生自灭地伫立,无声无息地萦绕,有如暗夜里支离的浮云,飘漂浮荡。但在骚动不安的追求中,那些俭朴的单纯的永久的风物所盛载的欲行欲止的感情,欲凝欲散的气氛,又让你心灵的归宿找到寄予的圣地,于尘世中窥一点儿香雪,渴饮一份盼望的甘露,心底陡生清冷。那几分人生的苦闷与凡间的驳杂淡淡地化解,在静默中渐悟了。
2019.12.19刊定
[作者简介]张 枫,笔名汴梁客子逸,河南杞县人,中学期间开始写作并颁发作品。在《南边周末》,《珠江夜报》,《跨世纪》,《东京文学》,《大观.诗歌》,《开封日报》,《汴梁晚报》,《京九晚报》等省表里报刊及省市广播电台颁发播出各种文学作品一百多篇(首),后停笔多年。比年重拾写作,在国内几十家网站和民众号平台颁发诗作和散文小说。系开封市作协会员,2003年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员,民众号平台《子逸物语》开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