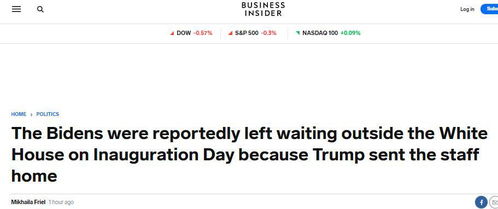梦 里 黄 昏(小说林)

梦 里 黄 昏
原创 汴梁客子逸 子逸物语

秋阳悄然默默地燃烧一天之后,显得很疲乏地悬在乡村西旁那片槐树丛间,逐步地摇动着,彤红而浑圆。正在隐灭的白天渺茫地忧闷地凄艳地泛着病色的红晕。暮霭从远的天外缓缓袭来,缕缕晚烟冉冉腾升,缭围着寂孤寂寞漫衍的人家。薄薄的风割开去,蒙起一层蝉羽般的轻纱。
斑斑驳驳的光里,咿咿呀呀摆荡着的伢崽蹒蹒跚跚着跑成雪球般。望见本身门前那株槐树,两只小腿飞滚得更快,竹篱门推开,娘呀娘便唤叫不绝,惹得栓在院当中的驴也和着欢嘶几声,长长的音耽搁开去平地起个重重的惊惶。
“放学了?……”做娘的闻声奔出,头上白雪身上洁白,一边叫乖乖一边慌慌拍打儿子身上滚的灰尘,嗔怪的在儿子脸上亲个不敷,“这又给谁打闹了一身土。”
儿子摆脱母亲饱满的度量,躲闪着母亲潮湿的嘴唇,摆荡着小腿去盘弄刚从灶房套间卸下的驴的大耳,嘻嘻了又嘻嘻。
院里暗下来,母亲给摇头晃耳打着喷嚏的驴添了一把草,回过头叫伢崽,”打盹了就去睡,明儿早起早来上书院去。老师说你这两天国上老闹打盹,是不是……”娘看着伢崽的一双眼睛很亮眼珠很美,伢崽盯着娘的两只黑眼球便亮晶晶一动不动。娘被瞅得竟欠好意思,拥了伢崽到堂屋里,摊他在床上。
“娘,你也睡。”
“好,好”
“娘,彻夜不推那磨。”
“好,娘彻夜不推那磨。”
“爹该回啦吧。”
“该啦。”
“爹怎么老长一段不返来,也不捎那带戳的纸。”
“爹忙。爹为伢崽出去挣钱,挣钱娶媳妇。“
“要爹不要钱,不要媳妇要娘。”
娘的眼眶里便噙一滴泪,晶晶亮。蓄满了便汪汪涌出,逐步沿悦目的脸流下,落在被上,落在娘握着的伢崽的手上,透亮的转动着。
伢崽骇了,生疏地望娘。娘便旋转了身,哆嗦了肩。许久,又逐步转过身来哼一支歌谣,高崎岖低,含模糊糊且又断断续续,一遍遍。孩子不语言,悄然默默地听,牢固得令人垂怜,眸子棋子似的黑。娘握着一双小手只是唱,长的黑发便在肩头窜流,遮着半个秀气的脸。伢崽总想瞧娘躲闪的眼珠,却又总不得见。做娘的守着牢固的崽,歌子唱到十遍,抽了手望,伢崽却不知何时睡熟,微启的嘴唇时常噏动,呼吸安稳而平静。
娘便盯了眼望儿。许久,轻轻离了床沿,到窗台上拿起了条帚和那张补了又补的铜底的面箩。
伢崽醒来,翻了身又不见娘。侧耳听了,便知娘又在隔邻的灶堂里赶了那驴在一圈一圈地走。伢崽却不起家,只是瞪了又黑又亮的眼,望床头木箱上那笼着晕黄的灯盏。灯已经结了花,灿灿的红,光却愈来愈暗。伢崽复侧了身向墙,望那斑驳陆离的泥壁。壁上有很多变化的面貌,有很多的眼睛在移动、跳跃,飞翔。他以为极有味而晕眩,面前的统统彷佛都在扭转,好像和一班孩子玩了一阵盲盲转蹲在地上展开双目之后;好像和娘一路推完那扇轰轰转动的石磨靠在磨盘上休息时分。
壁上的图象缓缓活了,向他笑哈哈地走拢来。先是一群浮现伏下翩翩起舞的五彩蝴蝶,在面前脑后扑来扑去;又成一群穿着彩衣炫舞的女儿,大概也便是娘讲过的神话中的那些个仙女,持着长长的五色丝带围着一根圆柱挥来荡去。中有一个生满头金发穿一条 拖地长裙飞旋了结总也看不清她的容面。伢崽急了,只想用手去拽了她衣裙,定睛了结再不见人,只一壁实着实在的光光墙壁。樑下直直撑一根槐木桩,壁上高高吊挂爹的破皮袄,脱落羊毛处光光的硬板板。伢崽不去世心,高兴忍了要寻找那消失的觉得,眯了眼去望却不再现那奇怪景观,只听得灶堂里那驴拉磨的声响霹雳霹雳忽远忽近。娘吆喝驴的声调也真好听,和着驴蹄踏在铺了砖的悠悠磨道上,如敲击一阵有节拍的梨木梆子,如扣打僧寺里祷告时的那铜磬,倥倥作名,清澈脆悦。伢崽顿觉心驰向往,好像于那安静山谷去听一曲悠婉鸟鸣,低缓而不滞涩中断,高亢而不哗闹难听逆耳。
许久,却多了一声老太婆的叹息:“唉,长山婶,人在世可真难啊,真像这驴普通,老了只好卸下任你去去世,不杀你去吃去卖即是最好的。”
伢崽听出这是邻人,住在自家东边那片林子小屋里的二嫂。看年龄自个能喊祖母,辈分却比娘还低了一辈。她的儿子先前常和爹出外苦钱,这两年娶了妻却不见再出。
“二嫂。好歹是自家儿孙,总不克不及不去管在人前落个话短不是?……这两天在老家人们吃哩照旧老二家吃哩?……嘚儿,驾——”娘也叫老太婆为二嫂,甘心低上一辈,不知为啥?
“老二家哩。迷症家的二小子,这鄙人平生子(岁)呢,就非让我搂着睡。夜里常醒,哇哇哭叫。唉,遭罪哩。”
“迷症家的又怀上了吗?这两口儿……”
伢崽听得娘“噗呲”一声,但立即又忍着了笑。
“嗯,……我去他家抱二小子这才刚出门呀两口儿就又吹了灯,咦……那模样让我恶心,”老太婆絮絮叨叨且愤愤不屈,“还老喊粮食不敷吃啦有俩儿子不当啦?唉,一个懒似一个。瞧见媳妇全日装扮来装扮去,我就……”
“老家人们呢?”
“别说啦别说啦。这不昨儿个还骂我不公正哩那手指呀都点到我鼻子尖上,唉,养儿不知儿养难,先前他爹去世得早,我……我……,可甭说多子多福啦……啊,啊……”老太婆忽然呜咽起来,惹得怀里的小儿也哇哇大哭。
“……别哭了,二嫂,看吓着孩子。”娘一个劲的劝,又去哄那小儿,“乖,乖,别哭,别哭。……他会吃馍不?”
“不……别拿,他还不会。”老太婆止了呜咽,那小儿的嘴彷佛被什么堵了,俄儿也止了哭泣。便听得那老太婆哆嗦的声调:
“咦,你的奶还这么好。长山婶,幸亏你。唉……这孩子哪一夜不醒几次哩,我的不可了,不比你们手轻脚健的,他吸半天,又瘪又没水,总哄不住。”
“我……我也不可了。”伢崽模糊入耳得娘的声音变得羞涩而不正常。他的面前便马上望见一对肥硕的石榴果般的大奶,那是娘的,他最喜爱吃。从前他放学返来还常往娘怀里钻,娘总一手揽着他腰让他趴在怀里吃个够,另一手在他身上摩娑揉捏,从上到下,令他满身酥酥不想转动。实在,娘也早没了奶水,但他照旧想去吃。娘也便餍足他,任他把头在怀里上下拱,用手在怀里来回摸,光滑腻软柔柔。很多次,他从娘怀里仰起脸来偷偷望娘,娘眼里便全是泪,而脸却颇冲动颇幸福,红得特别红的悦目。伢崽内心开始痒痒,老以为那两只白生生的奶子在面前吊来晃去。他抬开始,却“咣”地撞在床头小柜上,撞得那上面的灯摇几摇,朦胧的光也跳几跳。
“……长山叔,又好永劫间没捎信了吗?”
“嗯。或许他真忙的很。”
“唉,也真是,出去好几年了,怎么信也不寄一封呢?对了,婶子,你也得防范些。现在这些男子啊!想当初迷症他爹就那样,撇下俩儿子给我,一去南乡几年没返来。厥后啊,我一探询探望,从那里返来的人说:他跟一个本地的未亡人好上啦,被人打断了一条腿便欠好意思返来。我一听说,便立马托人去找,谁知……唉,二十年啦,也不知他去世到哪去了……不外,长山叔是忠实人,大概不会出啥不对哩。”老太婆叹息着,语调深沉而悲凉。
“二嫂,他……长山他决不会做那种坏了本心的事儿。他,他……我为他守着伢崽一小我私家在家苦熬,也是为等他的信,等他的信哩……”娘忽然“哇”地一声哭了。立刻,夜空里的安静破裂了,但却只听哭了一声便忍住了,这是她用牙齿咬住了围裙。咬得极费劲,脊梁一耸一耸,像负重的那驴背。
伢崽对着墙的脸便抬起来,顺了墙壁逐步向上望。屋顶却也没有什么惊奇,像一只大鸟睁开的两扇巨翅,昏暗里隐约延伸着一根根的玄色羽翎,去世血普通颜色的肌肤上,布着隐约出现的筋骨。倒是家中的树做的常见的檩椽,通常的泥烧出的一般砖瓦。这两面巨翅彷佛静止的浮在半空,覆成阴暗暗的穹庐。伢崽感触了父般的威武和母样的慈祥。他乌亮的眼已满噙了泪,昏沉沉觉得一幅宽大帷幕正缓缓下垂,只想牢牢裹了本身微小的躯体。
娘真好。伢崽在模糊中依稀想起娘那宽大暖和的怀,望见她浮在雾中般悦目的脸。那张俊脸突然生长了满腮的硬胡茬,青青的乌亮。这不是娘而是爹。忽然,这张脸又不见而只剩一张喷着酒气和浓烟的大嘴,那嘴缓缓大起,把娘悦目的脸吞下。于是,天地间就只剩下一深不见底鼠洞般的玄色大穴。
伢崽“啊”一声便醒,睁了眼屋里照旧一片朦胧,屋外却仍不见亮。那灯花不知娘何时进来拨过,比先前光明很多。悄然默默地定了神,却明白听见灶堂里另有语言声,倒是娘和另一个男子。老太婆明显已走多时。娘的声不高却还听得见,她是在谢什么人。伢崽彷佛瞥见一个身子并不粗壮的男人在帮娘赶那畜生。那驴总不走,男人 却不会末路,竟卸了套栓它在门外,自个呼呼隆隆地推起那磨来。娘立在磨道旁,抬眼望那男人,忍着笑又满盈了感谢。
“嫂,嫂子,你,你也真够苦的,拉扯个孩子,种十几亩地不,不说,还,还要黑更子夜的煎熬。哼,长山那小子,有,有啥能,本事,不就会……会砌个墙凿眼磨吗?我,我……”男人口吃得锋利,令伢崽一听便知了是谁。
“虎娃子,你要来玩就来,不要再提长山。”
“嫂,嫂子,我,我着实是气不外。你,你多好个女人,又,又美丽又贤惠。要,如果我,巴不得天,天守……”
“你醉了,虎娃。按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又不笨,为啥还不找个密斯?”娘的声音很细,伢崽贴了墙才听得清。
被娘唤作虎娃的,是个王老五骗子儿,可他待伢崽却不薄。他会扎很多多少耐看的鹞子,会用泥巴捏很多美丽的鸡狗猫兔,还会吹一口动人的笛子。可爹从前却总说他懒,是二流子。见他从门前过便引了伢崽向屋里躲。可娘则说他醒目,心好,见他来便让伢崽给他拿爹待客才抽的好烟卷。爹走后,他便常来家串门,替娘干这干那,还做了鬼脸耍花招逗本身乐。伢崽不明确他为啥不娶媳妇却独独喜爱孩子。
“我,我就喜爱嫂,嫂子一个……从嫂,嫂子第一天嫁来,我,我就喜爱上……上了你”虎娃更加变得口吃得很,“如,假如……长山哥,哥再,再没信,我,我……咱俩就一搭……”
“又胡扯……你再胡闹,我就真生机了。”娘语言的声音有些进步,气味也喘得仓促。伢崽翻身想和虎娃去玩,却不知怎么懒懒得总起不得身,只以为胸上压着什么,眼皮涩得难睁。
“嫂,嫂子,你真不……知,知我心?唉……”虎娃已是唉声太息,且声音哆嗦。娘也是叹息连声,语调涩滞:“虎娃,天都这晚了。快,快走吧。我,我得等你长山哥,等他返来。哪怕他说声不……”娘的声音逐步低得令伢崽听不清晰。伢崽好像瞧见娘伏在门旁哆嗦的体态。
“嫂,你……别,别……我等,等你一辈子……”
“你,快站起来。快……,你……走吧。”娘的声音仓促而升沉,彷佛已发狠。
“嫂,嫂子,你答……允许我,允许我吧!”伢崽听见母亲躲闪的混乱脚步,又听得母亲带笑的嘻骂:“好,好了……滚吧。啊,你这头偷嘴的驴。”
开门拉门的声音。一阵渐重渐轻的脚步,杂着一长声极重繁重而苍老的哀叹。即而,夜空里竟响起了几句悲凉亢奋的唱歌,伢崽一句也听不懂,却也以为非常难过:
“俏郎君,原许我到三月三,茶蘼架下来等待,终日掐指头。又说到五月五,小虹桥边看龙舟,此话赴东流!还商定七月七,后花圃中手挽手,织女会牵牛……忘记三月三,哎呀呀,五月不回还,哎呀呀,七月空盼……哎呀呀,越思越心烦,哎呀呀,越想越凄切……终日折磨废损奴容颜,唉呀呀,哎呀呀……”
那声调令民气碎。伢崽恍然看到一个在月影里东摇西晃踉踉跄跄的体态,正穿过那浓厚的丝瓜架下,走出自家院子,走向月影深处。远远的,传来狺狺犬吠。
伢崽双手撑了上身要透了窗向外望。光光圆圆的背面在朦胧的灯光里闪着亮,这幼小胴体像一头肥胖扁圆生着绿苔的娃娃鱼儿,又像渡了铜釉的孩儿瓷枕。突然,他赤裸的身以为有些发暖,转头望,娘不知何时也回到了身旁,实着实在的。娘的柔软暖和的怀搂着他。他转过身,无言地把脸贴在娘胸前,娘儿俩便相依偎了坐在靠窗的床头,听那缓缓远遁去的戏文。
“……见新忘旧,该上刀山,皇天爷岂能容这亏心的汉。哎呀呀,痴心望你还。唉呀呀,谁知你没心肝。唉呀呀……”
那缕悲凉伤感的歌音在氛围里久久俊逸,伢崽的心也高高悬着,长长的睫毛一眨不眨地瞅着娘凝在月光里的脸,那柔和的端倪如玉雕石铸般缓缓变得坚毅,令伢崽的确忘却了是娘。
伢崽这一次是真正牢固的睡了,由于有娘的度量。在娘的怀里真痛快酣畅,他只以为是于一壁阳光普照的山坡上眯了眼瞌睡,任那牧着的驴儿悠悠在草地周游;又以为是在柔软如毡的沙岸上腾翻滚打,细看夕阳奇景。他发觉那夕阳真像家中那转动的石磨,在暗中里高速飞旋,忽然,那太阳竟缓缓发白,变幻成一只大鲸,天上那乌云翻卷成波涛汹涌的大海。鲸鱼寂静褪去长尾,身材逐步膨圆,小白眼睛缓缓消逝,成缓缓升腾的一灰色雾团,转动来转动去。他总也搞不清晰它是怎样样飞起。却听得雾团里有一苍老声音在向娘和他沙哑发问:“我家的磨那边去了?借我家那红石磨哪去了?……”
表面的天下早已开始在用电磨了,伢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家那磨是新凿的。磨盘该换了,不知为什么娘总不愿换成新的。
伢崽醒来,日头早上树杈,娘破例的没早叫他,她正抱着本身呆望,两眼红得特别。而在窗下,却不测地堆放了两扇没合在一处的石磨,自家那驴却也不见。
怪事儿,伢崽好不明确……
1989.3.10底稿于家乡苦雨斋
2020,2,23刊定于故宅听雨楼
[作者简介]汴梁客子逸,本名张枫,河南开封市杞县人,中学期间开始写作并颁发作品,在省表里报刊和省市广播电台颁发播出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作品数十万字。比年初涉网络,在国内几十家网站和民众号颁发新诗和散文及小说一百多首(篇)。微信民众号《子逸物语》开办人!系开封市作协会员,2003年度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员。